
我叫张开明,今年88岁。退休前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植所所长。1952年大学毕业后,我就投身到祖国的橡胶树植保科技事业,并为之奋斗了一生。我耳聪目明,思维活跃,我每天必读的两张报纸是《参考消息》《海南日报》,我一直关心着海南岛的热作事业、我们的橡胶大业,回顾近70年的风风雨雨,看今朝的成就,感慨万千。

1953年4月19日,华南垦殖局特种林业研究所综合调查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明阳湖农场考察时
与该场场长一起合影(右三排第一人为张开明)
大学毕业 成为一名天胶人
1952年9月,我毕业于湖北农学院病虫害系,持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门的介绍信,前往广州华南垦殖局报到。当时从事橡胶研究都是保密工作,不能向家人说的。
我的工作单位是华南垦殖局正在筹办的研究所。所里当时从广西、北京、江苏等地调进的研究人员和分配来的大学生有几十人,大都没见过巴西橡胶树,更谈不上橡胶树的专业知识。
为了使大家了解橡胶树的生态习性和栽培技术,1953年4月,所领导乐天宇教授带领大家从广州出发,到华南垦殖局下属的广西、粤西、海南农垦分局的橡胶试种点以及老胶园做科学考察,历时半年。
当时,我们在海南各地考察了两个多月,第一站是儋县的联昌胶园。胶园在牙拉河对面,当时没有桥,我们先乘车到西联农场,再徒步走到联昌河岸,用牛车把帐篷拉到河边,大家涉水过河,再爬坡到联昌。在老胶园内搭好帐篷,安顿好生活后,开始到儋县的所有老胶园和新植场进行考察,前后花了20多天。
在这里,我第一次碰到“打台风”。我们住在胶园里的五个大帐篷内,半夜狂风大作,不时有“咔嚓”“轰隆”的巨响,胶树被风折断倾倒。外面黑灯瞎火、大风大雨,没地方躲避,大家只好围在帐篷中间的柱子下面,挨到天亮才敢走出帐篷。
“打台风”时,牙拉河水暴涨,行人很难涉水过河。我们考察队一行好几十人的口粮,只能派人从那大购买后,运到河岸边。我们在河两岸的大树上拉了一条绳索,岸这边由几位会水的小伙子提着铁桶过河,装上米、菜,一桶一桶地拉着绳索推着铁桶运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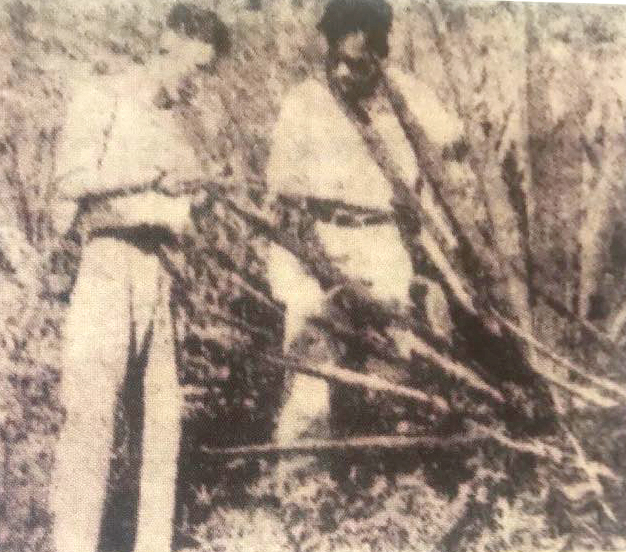
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经常到海南岛地区做调查研究工作. 热带作物研究所的张开明(右)、
周郁文在海南岛上检查剑麻的病虫害。(据1956年《光明日报》)
初到海南 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
最早要求研究所下迁海南是在1954年,后因故暂停。1957年10月,农垦部王震部长去日本考察,路过广州,到研究所召开会议,做了研究所一定要搬迁的指示。何康同志刚从北京调任所长,表示坚决执行搬迁的指示。
1958年3月16日,由何康带领第一批人乘车从陆路到海南联昌实验站。我是随何康走陆路的,坐木船过海,由海口转到联昌。
1959年,我爱人黄光辉调来,我们夫妇与加工系的何家灼夫妇合住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子。中间用竹片隔开,何家灼夫妇住里间,我们住外间。要煮点东西都在门口,地上架两块砖,权当炉灶烧火。
初到联昌时生活还不错,因为搬迁时,广东省委、海南区党委和儋县县委都表了态,要按照广州、海口或儋县县城的标准供应。但是好景不长,进入1959 年全国经济出现紧张形势,我们在联昌也陷入了困境。小卖部里的糖果、饼干都不见了,有几天甚至出现了断炊的情况。有一天吃了早餐,中午就没有米下锅了,于是刘松泉动员大家拿着镰刀、簸箕去胶园采割野菜,每人采5斤交到食堂。野菜收集起来,然后倒在一口大锅里,加清水和一把盐煮熟。刘松泉掌勺分锅里的菜,一人一碗。
实在饿得不行,我们还会到附近刚收割的木薯地里,去捡农民不要的小块木薯,用刀砍下没收完的木薯根头,回来洗净煮熟一人分一碗。当时还煮木薯嫩叶吃,有人还吃橡胶种子。
幸好,何康外出回来后,即发动大家种木薯和瓜菜,几个月后有了收获,填饱肚子没有问题了。
1959年,每人每月只供应19斤大米,一年没有吃到猪肉,连油也没有一滴,因此不少人患了水肿病。当时儋县的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大家的情绪仍然很高,没有一个人当逃兵,而且各项科研教学工作都正常地进行——这就是我们的“两院精神”,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1962年,我转到西华农场一个生产队做麻点病防治实验。当时的技工是黎传松,我俩踩着单车,提着喷雾器和农药跑了20多公里。那时队里的生活也很艰苦,一天两碗稀饭,胃里总是空荡荡的。有一天晚饭后,我俩提着水桶到田边的水井洗澡,看到很多小青蛙。黎传松说,抓小青蛙吃吧。他手脚麻利,用手抓,用脚踩,我在后边跟着捡,很快就抓了一小桶。回到队里,我俩向厨房工作人员要了一把盐,煮了一锅,吃了个饱。时隔40多年后,黎传松还常常提起那段艰苦的日子。

1990年,张开明主持热带作物学会植保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
三次交锋 根治橡胶溃疡病
第一次交锋从1962年12月到1967年,是在海南岛上。1962年秋冬季节,海南17个农场爆发橡胶树条溃疡病,30多万株橡胶树的割面树皮严重溃烂,各级领导都很震动。为此,华南热作所决定立题研究,由我和郑观标负责。我们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综合防治措施,在全省农场推荐。该措施对海南各农场减少烂树损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次交锋是从1971 年3月到1975年,还是在海南岛上。1970年冬,海南大多数农场橡胶树条溃疡大爆发,造成350万株橡胶树割面树皮严重溃烂。农林部领导两次派调查组进行调查。1971年2月,上级要求我展开针对性的研究工作。我一方面组织力量调查患病原因,一方面开展病树处理工作。1971年下半年,我协助兵团生产部在东岭农场召开第一次橡胶植保会;1972年在西培农场办点,协助兵团生产部召开橡胶树条溃疡病现场会;1973年在龙江农场蹲点开展新农药实验;1974年协助兵团生产部在卫星农场召开病树处理总结会,编印下发橡胶树条溃疡病基本知识小册子;1974年在海南组织6个防病工作组,以6个农场为基点,带动各农场开展防治活动。从此以后,海南各农场再未出现橡胶树条溃疡病大量烂树事故。
第三次交锋是1982 年到1984年,在云南西双版纳。1981年农垦部生产局指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派人去西双版纳,了解近年橡胶树条溃疡重病原因和协助开展防治。我和黄庆春去了云南,到9个农场18个分厂进行橡胶生产和病虫害问题的实地考察,分析了1978年-1980年橡胶树条溃疡病的重要原因,并提出防治意见。回院后,我们于1982年1月写了《云南西双版纳垦区橡胶病害调查报告》上报,农垦部生产局很重视我们的建议,为我们申请到一大笔科研研究经费。
通过1982年-1984年连续三年的防治实验工作,基本上控制了季风性落叶病区的橡胶树条溃疡病,而且保证了重病区能安全割胶生产,并且逐年增加干胶的产量。

1991年,张开明(右)为海南农民鉴定瓜菜病害并提供防治技术。
感谢妻子 我并不是称职的丈夫
1959年,为了支持院附中教学,我爱人黄光辉被院里从武汉借调过来,当时说好的是借调一年。
我与爱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她本来在武汉高校任教,我知道她肯定会来,但没想到她是那样坚定:“广州种不出橡胶树,当然要往海南走喽,我们听党的话跟党走。”没想到,这一借就是一辈子,我们再没离开“两院”,没离开海南岛。
那几年我长年在外出差,年头走年尾回,三个孩子出生时,我都没有守在爱人身边。
第一个孩子出生那年,我在西双版纳工作。当时交通特别不方便,我爱人快要临产时,她自己搭院里运输橡胶胶片的大卡车前往海口。她大着肚子坐在车斗里的胶片上,五六个小时,一路颠簸到海口,然后她再坐船离岛,回武汉娘家生孩子。后面的两个孩子,她都是这样过来的。年龄大了,退休了,我们有时间坐下来回忆过去的事情时,每当我想起爱人的这段经历,心里格外不忍,也十分心疼。
其实,白手起家发展天然橡胶,同事们的工作状态与我是一样的,大家都是这样玩命干工作的,我们身后的家人,默默支持着我们。在艰苦的岁月里,我们那一代人没有一个逃兵,全部坚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今年,我88岁了,身体还不错,就是腿脚不灵便。那是年轻时在西双版纳出差时,在梯田间滚落的后遗症。当时年轻没觉出什么,几年后便感觉不对了。现在,我出行更多地依靠轮椅,生活上全靠爱人照顾。我为祖国的橡胶植保事业奉献了一生,我爱人为了我,为了“两院”附中的孩子们,付出了青春,我们共同见证了祖国的橡胶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现在成为全球第四大橡胶种植国与生产国,这是一份有意义的事业,我们很自豪,也很欣慰。
讲述人:张开明
讲述时间:2019年10月28日
南海网首席记者 康景林








 琼ICP备11000394号
琼ICP备11000394号 琼公网安备 46010602000325号
琼公网安备 46010602000325号